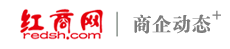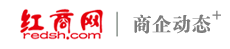更重要的是,随着新业务的拓展,万科内部也遇到一些发展瓶颈。
李飞从深圳总部调至北京公司两年后,他的奖金只有在总部时的1/5,而奖金在总收入中占70%,折算下来总收入被腰斩。
当各种新业务在万科40多个分公司零星发展起来的时候,总部并不扮演亲力亲为的“家长”,而是坚持做裁判员,监督比赛。在万科一条重要的准则就是员工奖金与“ROE”高度相关。所谓“ROE”是指取得的利润回报和占用的资本量之间的比率,它和资本周转速度有关,在房地产这种对资本有着高需求的行业,周转速度是关系公司生死的。
李飞解释说,“北京一笔钱转一圈要3年,在南方有些城市钱转一圈不到1年,同样是一笔钱的效率,南方城市赚的利润是北京的3倍,直接影响了收入。”
对此,李飞能够理解,但不见得能够接受。“这也是万科市场化的体现,它要强调对所有的事情公平。”他说,郁亮和王石最大的不同在于郁亮更为“实用”,对纪律性的要求很高。李飞最终选择了离开。
在2014年之前,万科支付给员工的薪水不算高。“进入万科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状态,在价值观上高度认同,比如不腐败不行贿,能够以万科为自豪,否则你就对抗不了比同龄人工资低的问题”,王珂在万科工作了3年,最终也选择了去商业地产代理销售公司誉翔安,“年轻人其实还好,但对于有职业经验的人来说,收入要比同行低接近一半。”
新业务的试水,考核标准的探索,也使万科的内部运行出现一些矛盾—而这一切,也恰恰是2014年万科进行变革的前奏。
郁亮在不断反思:万科赖以高速成长的“职业经理人”制度,是否再适用于新时期的发展?
答案很明确,现在的万科需要一种共担的机制,让团队利益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,以对抗行业动荡时期产生的风险。“过去黄金时代基本上不会有失败,转型的时候付出跟得到就未必挂钩,会有失败。”
过去两年,他的名字不断和一些互联网公司同时出现在媒体文章标题上,比如他带领万科高管拜访了腾讯、华为这类IT公司,或者小米、阿里这样的新兴互联网公司。一时间,大家并不能真正看清楚他要做什么。
事实上,通过对不同技术公司的拜访,郁亮深受启发。
“我看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‘扁平化架构’‘去金字塔’‘去精英化’”郁亮说。这个洞察触发他思考把合伙人制度引入万科,以此解决内部激励问题。而在国内传统产业的企业里,还没人这么做。
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风险或许是无法完全规避的。郁亮成立了一个“试错小组”。
这个小组的七八名成员,来自总部不同部门。每周一上午,这个一周最宝贵的时间,他们都要在郁亮的办公室开会。合伙人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,试错小组都会尽快给出反馈和调整。
“你们看到的时候,这个事情已经启动了,但我们的确想了很久。”郁亮说,他这几年都在为合伙人制度的启动做准备。
在初步计划里,某个层级以上的管理层用前一年奖金中的一部分去二级市场购股。毫无疑问,这有风险,首先是奖金会减少,而这部分损失的奖金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也并不确定。对于一些员工的犹豫,郁亮决定直接面谈。“我去了所有的一线公司,跟他们谈,”郁亮说,“如果你自己都没信心,那你为什么还选择在万科呢?”郁亮反复强调说,他只是要求某个层级以上的管理层购股,并没有强制所有人。
经过沟通,更多的公司人不抗拒这样的机会。“它给了一个更大的杠杆,是一个创富的机制,能不能创富在于所有的合伙人能不能把业绩做上去,做上去的话,未来的收益还是非常可观。”万科杭州分公司的宗卫国透露,以一线公司经理这个级别,他用了约1/5的奖金去认购股份。
包括宗卫国的奖金,万科超过1300人的经济利润奖金都被交给一个名为“盈安合伙”的公司在二级市场购股,购股后,截至2014年12月中旬,这些合伙人占公司总股份数3.3%,成为万科A的第三大股东。“我知道赚钱多少是一回事,关键在于有没有参与感,这个事很重要。”郁亮说,合伙人解决的是员工们的身份问题。
“这还是一个筛选的过程,筛选对万科认同的人,是一个重新聚合的过程。大家用钞票去投票,这是一个积极举措。”即便远离了这家公司,王珂仍然会观察这家公司发生的细微变化。
目前来看,合伙人制度的确让员工们更大程度上去“共担”公司盈亏。以6月底前后合伙人购股的价格计算,当时每股8.5元左右,到12月中旬11元多的价格,股价上涨接近40%。虽然2014年分红计划还没有公布,而万科从2013年起就提升了股东分红,以2013年每10股派送红利4.1元来计,分红比例接近29.87%。
公众公司并不自由,任何决定都需要等待资本市场的反应。当今年6月万科B转H股之前,资本市场对于全新的合伙人制有些质疑态度。而郁亮在3月增持万科股份,也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质疑声。“资本市场首先要看我个人对公司的信心,那么我增持,还要看管理团队对于公司的信心,”郁亮对《第一财经周刊》回忆说,“我们推出了合伙人,如果单一持股,公司可能会以市值管理为借口来做很多事情。”
为此,万科的“试错小组”还设计了项目计划与之配合,“如果仅仅是项目跟投,很有可能短期自利行为会发生,投资人会质疑我们是不是侵蚀它们的利润。”
郁亮的财务背景在万科的改革过程中日益显示作用。
俯瞰一家房地产公司,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数百个项目的组合,而万科是一个由三四百个项目构成的组合。在这项项目跟投计划里,万科设定了一个层级,在这个层级以上,所有成员必须跟投所在地的所有项目,而跟投数量由当地公司成员自己协商,“假设一个公司有10个项目,每个项目最少要投入30万元,他必须得每个项目投足那么多钱。”郁亮介绍,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只是为了防止作弊行为的发生,避免某个管理层因为跟一个项目利益关联更大,而将资源倾向该项目。
事实上,合伙人制度带给万科的不仅是员工身份的变化、以及利益的捆绑,还能松动复杂的管理结构,从而提升团队效率。要知道,大公司病的一个典型症状,便是冗余的层级—而伴随合伙人制度同步推广下去的,正是一线公司的层级精简计划。
“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中心,公司的资源和他的关系是对话和辅导的关系,”作为万科一线公司高管,宗卫国对这种层级精简深有体会,“很多事情就容易变成两层架构,责任人和参与人,责任人对结果负责,组织其他同事一起去做一件事,上一级领导只是指导他,但并不对结果负责。”
作为一线公司管理层,宗卫国的工作量从今年三四月推行合伙人制度以来减少了。“我过去的主要工作是解决下属没法解决的疑难杂症,搞不定的来找我。现在的工作是怎么给团队设置任务,然后怎么辅导他们把工作做好。”
不仅仅是公司内部,万科还将这项制度推广至合作伙伴。就在杭州公司说服合作公司的高管向项目入股,正准备作为“合作示范区”向其他地方公司推广时,它们发现对手楼盘因为动工时间早有可能先开盘。以往,它们需要花很大功夫去说服合作单位,包括增加薪水赶工期,而这一次仅仅因为对方入股,最终楼盘完工时间比对方早。
好几个和万科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,郁亮是少见的“不焦虑”的企业家。“中国大部分公司最大的动力来自于追赶,因为别人过得好,要做成它们那样的公司,从而在公司内诱发集体共鸣,这种企业里面天生有种恐惧和焦虑。”在王珂看来,当公司扩大到40多个分公司,与几百个合作单位有交集时,很难依靠一种理念去形成共鸣,而利益捆绑成为最有效的方式。
共3页 上一页 [1] [2] [3] 下一页
万科新帅“三把火”攻坚马年 布局全系产品重回一线
万科商业地产再下一城:首个商业交割麦格理
万科影响行业九大选择:合伙人、商业地产、全民营销
万科福州一楼盘未取得预售许可证 被指违规出售
万科、绿地、恒大仨龙头房企“北京分舵”换将
搜索更多: 万科